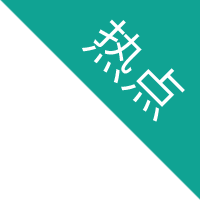目前,我国对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尚未有明确法律规定。与此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条文为《婚姻法》第四条,该条规定“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之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此条文作为《婚姻法》总则部分的最后一条,仅仅是关于道德义务的倡导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即使违反,也无需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因为法院无法通过判决的形式强制当事人履行道德义务。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但在司法实践中,签署夫妻忠诚协议、并依据协议要求违反协议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支付赔偿的案例却层出不穷。夫妻忠诚协议的约定形式及违约后果,也千差万别。有的涉及婚姻关系的解除,有的涉及共同财产的分配,有的涉及子女直接抚养权的归属,有的涉及巨额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支付……尽管,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作出了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但上述情形,不足以包括违反忠诚义务的全部情形,例如偶而的出轨、嫖娼、通奸、婚外情等行为;或者即使是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但未导致离婚的。因上述行为而主张违反忠诚义务一方赔偿损失的,将没有法律依据。
当事人普遍签署的夫妻忠诚协议无法可依,以及不同法院对不同形式夫妻忠诚协议的判决结果不尽一致,是我国司法界亟需解决的法律问题。
二、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的不同观点
夫妻忠诚协议,是指夫妻双方在结婚前及/或结婚后,为保证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违反夫妻忠诚义务为目的,以书面形式约定违反协议一方将承担违约责任或赔偿责任的协议。约定责任的常见形式有支付违约金、赔偿金、欠款,解除婚姻关系,财产归另一方所有,子女直接抚养权归另一方,“净身出户”等。
我国学术界对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的态度,总体而言可分为无效说与有效说两类。
(一) 无效说
持无效说观点的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否定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
第一, 忠诚协议异化了本应表现为包容、理解与关爱的婚姻关系,将精神层面的追求一致演化成为物质上的交易,不应被鼓励。如果用协议的违约后果,代替双方经营婚姻的努力来约束婚姻,将产生错误的婚姻价值导向。
第二, 忠诚协议约定给付的内容大多与身份关系有关,如是否解除婚姻关系、子女直接抚养权的归属等等,并不具有可执行性,也不应该允许用协议和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来束缚当事人变动身份关系的自由意志。当事人对自己婚姻关系的变动有自由选择权,合同不能限制这种法定的权利。
第三, 夫妻忠诚协议并非双方在冷静、理性的情况下签订,往往掺杂着情绪化的情感因素,也掺杂着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法量化的努力和付出,以及其他影响夫妻关系的因素。在结婚前或者婚姻初期,双方爱情至上,为了表达爱意容易订立后果严重的忠诚协议。尽管签订协议时可能表达了双方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但订立此种协议往往具有非理性的成分,不能将此协议等同于平等关系主体订立的纯粹调整财产关系的合同。此外,在订立协议时,也不一定将所有影响协议后果的因素全部罗列在内。在夫妻感情出现问题后,如果仅以夫妻财产协议内容为索赔依据,显然不公,会对法律及司法权威造成不良影响。
第四, 目前我国的损害赔偿原则还是填补原则,而非惩罚性赔偿原则。如果允许当事人事先约定损害赔偿的后果,势必产生有钱人可以用能够承受的金钱代价肆意违反忠诚义务、损害他人权利的后果,这将造成人们因财富的多寡不同而享有不同身份性权利的不平等局面发生。
(二) 有效说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夫妻忠诚协议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就应当具有法律效力,理由如下。
第一, 婚姻法属于私法,应当秉持私法自治、法无禁止则自由的原则。夫妻忠诚协议是私法自治原则在婚姻法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认可其效力,契合了私法自治的理念。
第二, 夫妻忠诚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是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延伸,法律应当予以保护。认可夫妻忠诚义务的效力,并不是限制当事人变更身份关系的自由,剥夺当事人变更身份关系的权利,而是在当事人选择变更身份关系后,需要按照自己当初的允诺,承担相应的财产性责任。因此,夫妻忠诚协议更多的还是具有财产属性,而非人身属性。
第三,当事人在结婚前或者结婚初期,在法律强制性规定之外,自愿承担违反忠诚义务的违约后果,如果法律赋予这种约定以强制力,将更有利于当事人考虑违反忠诚义务的代价,维护婚姻的稳定性和忠诚性。当事人有权选择是否签署忠诚协议,有权选择是否需要承担违约后果,但一旦作出选择,就应当按照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将促使当事人在签署夫妻财产协议、在选择是否离婚时更加理性。
三、明确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的建议
笔者认为,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原则上应是有效的。理由如下:
第一, 夫妻忠诚协议的存在与婚姻的核心价值并不冲突。婚姻关系的存续需要爱情与责任,需要夫妻双方互相关爱、理解和包容,通过双方共同努力、用心经营,才能维持婚姻关系的稳定和长久。夫妻忠诚协议的存在,并不与上述价值观相违背。相反,在双方追求精神层面的目标一致之外,在出现感情问题后,办理离婚手续之前,一方因为夫妻忠诚协议的违约后果,重新考量婚姻存在的必要性和离婚的代价,将有利于一方当事人作出更理性的判断和选择。法律赋予夫妻忠诚协议效力,并非剥夺当事人变更身份关系的自由选择权,而是要求当事人在行使选择权后,需要按照承诺承担相应后果。这将更有利于促使当事人在选择结婚对象、订立夫妻忠诚协议、选择是否离婚时更加趋于理性。
第二, 法律是最低要求的道德标准。当事人在结婚前,应当明确忠诚义务是夫妻之间应当相互履行的最低义务,从而考虑是否要选择结婚。即使《婚姻法》第四条所规定的夫妻忠诚义务一种倡导性规范,也不妨碍夫妻双方自愿以协议的形式将此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只要此种协议不违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法律就应当承认其效力。
第三, 损害填补原则只是法官在确定侵权赔偿数额时应遵循的规则,该规则对当事人并无强制力。司法实践中许多侵权行为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就具体赔偿数额进行协商,并达成了高于或低于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协议,法官并不会因其违反损害填补原则而否定其效力。
如果要求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必须与损害发生的数额相一致,则协议将没有存在的必要。在夫妻关系中,一方违反忠诚义务,其实际损害后果是无法量化的。在签署协议时,双方协商约定的违约责任或者赔偿责任,是双方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对对方的爱护程度、自愿受到的惩罚后果及其他因素作出的综合判断和考量。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第三方利益,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
综上,笔者建议,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同时,也应当明确夫妻忠诚协议的生效要件、必备条款,在一定条件下,还应当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一、夫妻忠诚协议应当具备特别的生效要件。
夫妻在同一环境中亲密长久生活,存在一方因生病、醉酒、睡觉等处于不清醒状态而需要被另一方照顾的情形,因此,应当对夫妻忠诚协议生效要件作出比一般合同的生效要件更为严格的规定。比如,协议必须经过公证程序方能生效,以保证协议的内容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此外,夫妻忠诚协议必须以婚姻关系成立为生效要件,情侣之间的忠诚协议,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以保证婚姻的严肃性和神圣性。
二、法律应当列明夫妻忠诚协议的必备条款。
鉴于实践中当事人自行约定的夫妻忠诚协议形式各异,为了保证协议内容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执行的可操作性,应当明确夫妻忠诚协议必备的条款。如,需要以列举的形式明确“不忠诚”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不能简单笼统地表述成“不能出轨”或者“违反忠诚义务”。违约后果,也应当保证可以用财产量化的标准加以衡量,禁止不具有强制执行性、或有损子女利益、或具有人身侮辱性的违约责任的约定,比如违约方需下跪道歉、在公众场所喊口号、禁止探视子女等。
三、在一定条件下,赋予法官一定范围的自由裁量权。
为了保证夫妻忠诚协议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应当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的一方在按照协议履行后,仍然能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且不影响其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和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例如,禁止“净身出户”条款的约定。夫妻忠诚协议条款的违约后果,虽然具有一定的惩罚性,但如果违约后果过于苛刻,严重损害另一方的基本生存条件,影响到由其赡养或抚养的人的生活条件,将给社会秩序造成不稳定因素,法官有权结合当地的人均收入状况和消费水平,对过于苛刻的违约后果做出适当调整。